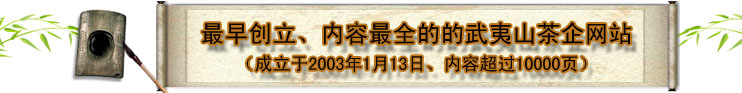|
熙宁年间,苏颂(字子容,谥正简,赐魏国公)出使北方辽国,姚麟为副使,对苏颂说:“何不携带一些小龙团呢?”苏颁说:“这是供奉皇上的物品,谁敢送给北虏之人。”不久,又有贵宦公子出使北辽,贮积了很多团茶带去,从此北辽就非团茶不收,非小龙团就不以为贵了。他们那里用两个团饼交换蕃罗一匹,我们这里却为得到蕃罗一匹交给四个团饼作为报酬,稍微不满意,当即形于言语。近来又有皇帝身边的近贵巡守边境,更是以大龙团作为常供,而以密云龙作为好茶罢了。
南宋罗大经《鹤林玉露》记载:岭南人以槟榔代替茶叶。
北宋彭乘《墨客挥犀》记载:蔡襄(字君谟),谈论茶事的人没有敢于对他发言的;这是因为建茶之所以名重天下,都是由他创始的。后来他又制作小团,其品质比大团更加精致。有一天,福唐(今福建福清)蔡叶丞秘密派人邀请他品啜小龙团茶。坐下品茶很久,又有一个客人到来,他品味着茶说:“这不仅仅是小团,一定有大团掺杂进来。”蔡叶丞非常吃惊,急忙呼唤童子来责问,回答说:“本来碾造的是两个人的茶,后来又有一个客人到来,再造来不及,就以大团掺杂奉上。”蔡叶丞极为叹服他的精审鉴别。
王安石(封荆国公)担任翰林学士的时候,曾经去拜访蔡襄(字君谟)。蔡襄听说王安石来,非常高兴。取来绝品茶叶,亲自洗涤茶具、烹点佳茶款待王安石,希望他能予以称赏。王安石从夹袋中取出消风散一撮,投入茶瓯中一并饮用。蔡襄大惊失色。王安石慢慢说道:“这茶味道太好了。”蔡襄大笑,同时叹服王安石的真率。
南宋鲁应龙《闲窗括异志》记载:当湖(位于今浙江嘉兴平湖城东,一名东湖、鹦鹅湖)德藏寺有水陆斋坛,是以前富民沈忠所修建的。每次设斋祭祀时,如果施主虔诚,茶中就会出现瑞花。其花纹俨然可见,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。
南宋周辉《清波杂志》记载:我的父亲曾经向张祁(字晋彦,号总得居士,张孝祥之父)寻觅佳茶,张祁以两首小诗作答道:“内家新赐密云龙,只到调元六七公。赖有山家供小草,犹堪诗老荐春风。”“仇池诗里识焦坑,风味官焙可抗衡。钻馀权幸亦及我,十辈遣前公试烹。”当时张祁偶然得病,此诗由其子代书。后来错误地刊刻到张孝祥《于湖集》中。焦坑茶产于庾岭之下,茶味苦涩而较硬,许久才回味甘甜,正如苏东坡《南还回至章贡显圣寺》诗中所咏的“浮石已干霜后水,焦坑新试雨前茶”。后来我曾多次得到这种茶,本来不是什么精品,只是当地人自以为重,包装之后钻营进奉权贵,其品质怎么可以比得上建溪的绝品呢?
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:旧曹门街北山子茶坊,其中还建有仙洞、仙桥,京城的士女往往夜间到此游玩、品茶。
宋人《五色线》记载:骑火茶,寓意不在火前,也不在火后。清明节改火,所以叫做骑火茶。
北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:王城东一向厚待的只有杨大年。他有一个茶囊,只有杨大年来了,才取茶囊准备上茶,其他宾客不能享受此等待遇。
明代慎懋官(字汝学,湖州人)《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》记载:宋朝徽宗、钦宗两位皇帝被金人俘虏北行,到一座寺庙中,有两个石雕的金刚并排拱手而立,神像高大,头部几乎顶到房梁和屋椽,没有其他的供器,只有石雕的钵盂、香炉罢了。有一个胡人僧侣出入其中。僧人作揖坐下来,问从何来,两位皇帝回答说从南边来。僧人就呼唤童子点茶进奉,茶味非常馨香甘美。两位皇帝想再索要饮用,僧人和童子却向后堂走去。等待一个时辰还不出来,进去寻找,却见寂然空屋,只有竹林间有一个小屋,屋中立有石刻的胡僧像,两个童子侍立两旁,仔细观察,俨然与刚才献茶的僧人、童子一样。
宋代马永卿《懒真子录》记载:王元道曾经说过:陕西子仙姑,传说修得道术,能够不吃饭。年纪看起来大约三十多岁,不知道真实的年龄。陕西提刑阳翟(今河南禹州)人李熙民逸老是一个正直刚毅的人,他听人们传说得非常神奇,就亲自到青平军进行考察。见面之后,看到仙姑道貌高古,不觉心服。于是就说:“我想给您献上一杯茶,是否可以?”仙姑说:“我不饮茶已经很久了,如今就勉强品饮一次。”饮茶之后,不一会儿垂着两手出来,白得像白玉、白雪一样。很快,只见所饮的茶从双手的十个指甲中涌出,凝结于地上,色泽还没有改变。逸老命人就地刮取茶来,并且让他们品尝,香味如故,于是大为叹奇。
南宋朱熹《朱子文集》中有《与志南上人书》写道:偶然得到一些安乐茶,分送二十瓶奉上。
南宋陆游《陆放翁集》中有《同何元立蔡肩吾至丁东院汲泉煮茶》诗写道:云芽近自峨眉得,不减红囊顾渚春。旋置风炉清樾下,他年奇事属三人。
南宋周必大《周必大集》中有《送陆务观赴七闽提举常平茶事》诗写道:暮年桑苎毁《茶经》,应为征行不到闽。今有云孙持使节,好因贡焙祀茶人。
北宋梅尧臣《梅尧臣集》中有《晏成续太祝遗双井茶五品,茶具四枚,近诗六十篇,因赋诗为谢》。
北宋黄庭坚《黄山谷集》中有《博士王扬休碾密云龙,同事十三人饮之戏作》。
北宋晁补之《晁补之集》中有《和答曾敬之秘书见招能赋堂烹茶》诗写道:一碗分来百越春,玉溪小暑却宜人。红尘他日同回首,能赋堂中偶坐身。
北宋苏较《苏东坡集》中有《送周朝议守汉川》诗写道:茶为西南病,俗记二李。何人折其锋,矫矫六君子。[原注:二李,是指李杞和李稷。六君子,是指陈师道与其侄子陈正儒、张永徽、吴醇翁、吕元钧、宋文辅。由于当时蜀茶实行禁榷,危害于民,二李是其始作俑者,而六君子则是坚持正义抗论救民的。]集中又有《书参寥诗》写道:我在黄州,参寥(诗僧道潜,俗姓何,名昙潜,号参寥子)从吴中前来拜访,居住在东坡。有一天,我梦见参寥所作的诗,醒来后记忆其中的两句:“寒食清明都过了,石泉槐火一时新。”又过了七年,我出任杭州知州,而参寥也开始卜居西湖智果寺院。寺院中有一道泉水从石缝中涌出,甘甜冷冽,适宜烹茶。寒食节的次日,我与宾客乘船泛湖从孤山来拜谒参寥,汲泉钻火,烹煮黄茶,忽然感悟曾经梦见的诗,于七年以前已有征兆。各位宾客都非常惊叹,由此可知史书传记所记载的很多故事,并非虚语。
旧题苏东坡《物类相感志》中说:芽茶放盐,不觉苦咸却觉甘甜。又说:吃茶多会出现腹胀,可以用醋解之。又说:用陈茶薰燃,能很快驱赶苍蝇蚊子。
南宋杨万里《杨诚斋集》中有《谢傅尚书送茶》写道:承蒙您从远方赠送新茶,我当携带大瓢,汲取山溪泉水,收拾山涧中的败枝散叶,烧起折脚的石鼎,烹煮茶末,品啜香乳,以享受这天上仙人的恩惠。惭愧我胸中没有诗书文章,只是一味搅破菜园罢了。
南宋郑景龙(字伯允,三衢人)《续宋百家诗》中说:本朝孙志举,有《访王主簿同泛菊茶》诗。
宋代吕元中《丰乐泉记》记载:欧阳修访得酿泉(当为让泉,在今安徽滁州琅琊山)之后,有一天会聚宾客,有人献上新茶,欧阳修就命人汲泉煎茶。汲泉的人在半道上摔倒,泉水倾覆,就汲取其他泉水代替。欧阳修知道不是酿泉水,责问汲泉的人,才知道另外一个泉水在幽谷山下,于是命名为丰乐泉。
宋代赵令《侯鲭录》记载:黄庭坚(字鲁直)说:烂蒸同州(今陕西大荔)羊,浇上杏酪,用匕首边切边吃,而不用筷子。抹南京的面,作槐叶冷淘(凉面之类),加上襄邑(今河南睢县)的熟猪肉,炊煮共城(今河南辉县)的香稻,吃吴人的、松江的鲈鱼。吃饱之后,用康山谷帘泉水烹煮曾坑的斗品佳茶,品饮一会儿,仰卧于向北的窗户之下,使人朗诵苏东坡的前后《赤壁赋》,也足以称为快事。
《苏舜钦传》记载:苏舜钦流寓苏州,有兴致时就驾着小船出盘门、阊门,吟咏狂啸,游览古迹,江边的茶、乡村的酒都足以消除忧愁,荡涤胸怀。
南宋楼(字阳叔,号遇斋)《过庭录》记载:刘(字贡父)知长安,有一个叫做茶娇的妓女,以美貌智慧著称,刘为她所迷惑,其事曾经传诵一时。刘被召回京师,欧阳修(字永叔)出城四十五里前去迎接,刘因为酒醉未起。欧阳修调侃地说:“不仅酒能够醉人,茶也能够醉人。”南宋谢维新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记载:觉林寺的僧人志崇,制茶分为三等,招待宾客用惊雷荚,自己饮用用萱草带,供奉佛陀用紫茸香。凡是来赴茶会的,就要用油囊来盛剩余的茶水。
江南有一位驿站的官员,自以为办事干练。对太守说:“驿站的事务已经处理好了,请前去检阅指导。”于是刺史就前去视察,先到一个房间,是酒库,各种酒皆熟,室外悬挂一幅神像,问是何人,回答说是酒神杜康。刺史说:“您公务完成得绰绰有余啊!”又到一个房间,是茶库,各种茶品毕备,室外也悬挂一幅神像,问是何人,回答说是茶神陆羽(字鸿渐)。刺史更加高兴。又到一个房间,是菹(肉酱)库,各种砧板都有,室外也悬挂一幅神像,问是何人,回答说是蔡邕(字伯喈)。刺史大笑,说道:“这个不必设置。”江浙地区人们养蚕,都用盐藏在蚕茧中去缫丝,是恐怕蚕茧生出蛾子。每当缫丝完毕,就要煎茶叶为汁,把米粉捣碎,筛到茶水里煮成粥,叫做洗缸粥。整个家族聚集一起品啜,说是这样有益于第二年的蚕业生产。
宋代倪思《经堂杂志》中说:松声、涧声、山禽声、夜虫声、鹤声、琴声、围棋声、落子声、雨滴阶声、雪洒窗声、煎茶声,这些都是声音中的至清者。
南宋洪皓《松漠纪闻》记载:燕京(今北京)的茶肆中,设置有双陆局,正像南方人在茶肆中设置棋局一样。
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记载:都城临安(今浙江杭州)的茶肆中陈列有花架,其上安顿有奇松、异桧等花木,装饰店面,敲打响盏。另外冬天还要添卖七宝擂茶、馓子葱茶。茶肆的楼上,专门安排有妓女的,叫做花茶坊。
《南宋市肆记》记载:平康巷歌妓的馆舍,凡是初次登门的客人,就有专门提着茶瓶来献茶的,即使只喝一杯茶也要犒赏数千钱,叫做点花茶。
各处的茶肆,有清乐茶坊、八仙茶坊、珠子茶坊、潘家茶坊、连三茶坊、连二茶坊等名号。
谢府有酒,名字叫做胜茶。
南宋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记载:大茶坊,都悬挂名人字画;根据人之常情理解,茶坊本来应当以供应茶水作为正宗生意,但也有借此敛财,行为不当的。如水茶坊,其实就是娼妓之家,摆设水果桌凳,以买茶作为幌子,后生少年甘心费钱,称为干茶钱。又有提茶瓶(如上述的点花茶)和龊茶(官衙吏卒向店铺商人点送茶汤,强索钱财)等名色。
宋代杨伯岩《臆乘》记载:杨之编撰《洛阳伽蓝记》,其中说道:“饮食有酪奴。”是指茶作为酪粥的奴婢。
旧题元伊世珍《记》记载:从前,有客人遇到三茅真君,当时正值盛夏酷暑,三茅真君从手巾中取出茶叶,每人给一叶。客人品饮之后,感到五脏清凉。三茅真君说:这是蓬莱岛的穆陀树叶,众位神仙都作为饮品使用。又有宝文之蕊,吃了之后不会感到饥饿。因此谢幼贞有诗写道:“摘宝文之初蕊,拾穆陀之坠叶。”明代杨循吉(字君卿,一作君谦,号南峰)《手镜》(一作《奚囊手镜》)记载:宋朝的时候,姑苏(今江苏苏州)女子沈清友著有《续鲍令晖香茗赋》。
明代孙矿(字文融,号月峰,余姚人)《坡仙食饮录》记载:密云龙茶,极为甘甜馨香。宋寥正,又字明略,拜师于苏轼门下较晚,但苏轼非常器重他,目为奇才。当时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四人号称苏门四学士,苏轼对待他们都很优厚,每次到来,一定让侍妾朝云取密云龙茶款待他们。有一天,又命朝云取密云龙茶,家人以为是四学士到了,暗中观察,乃是寥正。黄庭坚诗中“云龙”,也是一种茶的名称。
《嘉禾志》记载:煮茶亭,位于秀水县西南湖中景德寺的东禅堂。宋代翰林学士苏轼曾与文长老三次经过湖上,汲水煮茶,后人于是在此建亭,以便标记胜迹。至今遗迹还存在。
明代曹学《名胜志》记载:茶仙亭,位于滁州琅琊山。宋朝的时候寺院的僧人为刺史(知州)曾肇(字子开,南丰人,曾巩之弟)所建,名称取自唐朝诗人杜牧(字牧之,号樊川子)的诗《池州茶山病不饮酒》中“谁知病太守,犹得作茶仙”的句子。曾肇有诗写道:“山僧独好事,为我结茨。茶仙榜草圣,颇宗樊川诗。”这是在宋哲宗绍圣二年(1095),曾肇滁州知州任内。
明代陈继儒(号眉公)《珍珠船》记载:蔡襄(字君谟)对范仲淹(字希文,谥文正)说:“先生的《采茶歌》(即《斗茶歌》)中写道:‘黄金碾畔绿尘飞,碧玉瓯中翠涛起。’如今的茶中绝品,色泽都很鲜白,翠绿乃其中下品罢了,想把‘绿尘飞’改为‘玉尘飞’,把‘翠涛起’改为‘素涛起’,怎么样?”范仲淹回答说很好。
又及,蔡襄嗜好饮茶,晚年老病不能饮茶,只是把玩罢了。
明代陈仁锡《潜确类书》记载:宋高宗绍兴(1131-1162)年间,少卿曹戬为躲避金兵移居南昌丰城县,他的母亲喜欢饮茶,起初山中没有井,曹戬就斋戒祈祷上天,就在院中屋后挖地,刚挖了一尺深,清澈的泉水就溢满涌出来,后人就把此泉叫做孝感泉。
五代后周显德(954-960)初年,大理寺卿徐恪,是福建建州(今福建建瓯)人,收到家乡书信并得到馈赠的铤子茶,茶饼表面有印文,一种叫做玉蝉膏,一种叫做清风使。
蔡襄(字君谟)善于鉴别茶品。建安能仁院有茶,生于石缝间,是茶中精品。寺院僧人采摘制造成八饼,称作石岩白,以四饼赠给蔡襄,另外四饼秘密派人到京城汴梁赠给翰林学士王硅(字禹玉,谥文恭)。一年多后,蔡襄被召回京城,拜访王硅。王命子弟在茶筒中选取精品碾制烹煮以款待蔡襄。蔡襄手捧茶瓯还没有品尝,就说:“此茶极像能仁寺的石岩白,先生怎么得来的?”王还不相信,索取帖子验看,于是折服蔡襄的鉴识之精。
明代冯应京《月令广义》记载:四川雅州(治今四川雅安)名山县蒙山(即蒙顶山)有五座山峰,峰顶有茶园,其中顶最高处叫做上清峰,出产甘露茶。从前有僧人患冷病已经很久,曾经遇到过一个老人询问其病情,僧人一一告诉了他。老人说:“为什么不饮茶呢?”僧人回答说:“本来以为茶叶性冷,难道能够治疗这种病吗?”老人说:“这里并非寻常的茶,仙家有所谓的雷鸣茶,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?”僧人回答说没有。老人说:“蒙山的中顶有茶叶,应当在春分前后多召集人力,等到春雷发声,一起采摘,以多为贵,到第三天就停止。如果收获一两,用本地的泉水煎服,能够祛除慢性疾病。煎服二两,就可以保证终身无病。煎服三两,就可以轻身换骨。煎服四两,就可以称为地上神仙。只要制作服用精致洁净,不会没有效果的。”僧人于是就来到蒙山中顶筑室居住等待,到了季节收获了一两有馀,还没有煎服完毕病就好了。可惜不能够在山上久住,从而更多地收获茶叶。从此身体康健、精力充沛,八十多岁,气力不衰。经常到城市中去,观察他的面貌就像三十多岁的年纪,眉毛头发都呈微红的墨绿色。后来进入青城山学道成仙,不知所终。如今蒙山五峰,其馀四个峰顶茶园都没有荒废,只有中顶上清峰草木繁茂,云雾缭绕,遮蔽日月,猛兽出没,人迹罕至。
明代陈继儒《太平清话》记载:张文规以吴兴(今浙江湖州)白苎、白洲、明月峡中茶作为三绝。张文规好学,有文采,苏辙(字子由)、孔武仲、何正臣等名士都与他交游。(此处当为错引,张文规当为唐代吴兴太守,有《湖州贡焙新茶》、《吴兴三绝》等诗,如何与宋代名士交游?)明代夏树芳(字茂卿)《茶董》记载:刘煜字子仪,曾经与刘筠一起饮茶。问左右道:“水烧滚了吗?”回答说:“已滚。”刘筠调侃说:“佥曰鲧哉!”(见《尚书·尧典》,意思说尧问谁能治水,大家都说鲧可以呀!)刘煜应声回答说:“吾与点也。”(见《论语·先进》,意思是孔子说我赞成曾点的主张。这里借“点”表示水开了,我来点茶的意思。)黄庭坚(字鲁直)以半铤小龙团茶饼题诗赠给晁补之(字无咎),诗中写道:“曲几蒲团听煮汤,煎成车声绕羊肠。鸡苏胡麻留渴羌,不应乱我官焙香。”苏东坡见了以后说道:“这个黄九,这么下去怎么会不穷困潦倒呢?”明代陈诗教《灌园史》记载:杭州歌妓周韶有诗名,喜欢收藏佳茶奇茗,曾经与蔡襄(字君谟)比试,品题茶的风味,蔡襄自愧不如。
江参,字贯道,江南人。他的形体面貌清奇瘦朗,嗜饮香茶,以为生活。
明代来集之《博学汇书》记载:司马光(封温国公,世称司马温公)与苏轼(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)谈论茶和墨。司马光说:“茶与墨二者的特性正好相反,茶要白,墨要黑;茶要重,墨要轻;茶要新,墨要陈。”苏轼回答说:“好茶、妙墨都很香,这是其品德相同;茶饼和墨锭都很坚硬,这是其操守相同。”司马光听后赞叹,深以为然。
元代耶律楚材的诗《在西域作茶会值雪》,有“高人惠我岭南茶,烂赏飞花雪没车”的句子。
明代顾元庆《云林遗事》记载:元代苏州光福乡富商徐达左,在邓尉山中建造养贤楼,一时名士都云集于此。画家倪瓒(字元镇,号云林,无锡人)来往尤其频繁,曾经派童子到山中担七宝泉水,以前面的桶水煎茶,后面的桶水洗脚,人们不理解其用意,有人问他,倪瓒回答说:“前面的桶水没有污染,所以用来煎茶;后面的桶水有时可能会为童子的泄气所污染,所以用来洗脚。”他的洁癖就像这样。
明代陈继儒《妮古录》记载:至正辛丑(1361)九月三日,与陈征君一同下榻愚庵师的房中,焚香煮茶,绘《石梁秋瀑图》,富有自由自在、超脱尘世的趣味。黄鹤山人王蒙题画。
明代周叙《游嵩山记》记载:见到会善寺中,有元代雪庵头陀《茶榜》石刻,每字直径三寸左右,遒劲魁伟,大为可观。
元代钟嗣成《录鬼簿》记载:王实甫有《苏小郎夜月贩茶船》传奇。
明代徐献忠《吴兴掌故集》记载:明太祖朱元璋喜好顾渚茶,但贡茶定制,每年只进贡顾渚茶三十二斤,于清明节前两天,县官亲自前去监督采制,进奉到南京奉先殿焚香罢了,不曾有其他的上供茶叶的规定。
明代郎瑛《七修汇稿》(当即《七修类稿》)记载: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(1391),诏令天下产茶之地,每年贡茶都有定额,以福建建宁(今福建建瓯)为上品,听任茶户采制进贡,不必通过官府。茶名有四种:探春、先春、次春、紫笋,不得碾碎研末制成大小龙团。
元代杨维桢(字廉夫,号铁崖、东维子)《煮茶梦记》记载:铁崖道人躺在石床之上,时过二更,月色微明,棉纸蚊帐上映着梅花的影子,也投到半个窗子,野鹤孤立而不鸣。这时派小芸童汲取白莲泉水,点燃枯湘竹火,授以云雾佳茶,烹点供饮。这种境界真如游心太虚幻境,使人仿佛进入梦乡。
明代陆树声《茶寮记》写道:在乡居的园中小轩矮墙的西面开一个小茶寮。其中设置茶灶,大凡汲水的茶瓢、煮水的茶罂、洗茶以及击拂等一系列茶具应有尽有。选择一个稍通茶事的人主持,另一人帮助汲水煎茶。宾客到来,就会看到茶烟从竹外隐隐升起。如果有佛徒禅僧过从,每每与我一起结跏趺坐,啜饮茶汁,清谈高论,而没有生分的话。时值深秋(农历九月)的望日之后,适园无诤居士(陆树声)与五台山僧演镇、终南山僧明亮,一同烹试天池茶于茶寮中,并随意记录下来。
明代吴文焕(一作秀水吴继)《墨娥小记》记载:所谓千里茶,是用一两五钱细茶、一两孩儿茶、一两柿子霜、六钱粉草末、三钱薄荷叶,研为细末调和均匀,炼制成蜜丸如白豆大小,可以替代茶叶,同时可以供外出远行饮用。
明代汤显祖(字义仍,号海若、若士,临川人)《题饮茶录》写道:宋初翰林学士陶谷说“煎水,是点茶的关键”。此语最得煎茶之道的三昧。国子监祭酒冯梦桢精通茶道,亲自料理洗涤、煎水之事,然后请客人品饮。宾客有讥笑他的,我调侃地为之解嘲道:“这就正像美人,又好比古代的法书名画,试想可以经过俗汉的手吗?”明代陆(字举之,号少石子,鄞县人)《病逸漫记》记载:皇太子出阁听讲,一定要派左右去迎请讲官。讲完之后,则要对东宫的官员说:“请先生吃茶。”明代焦(字弱侯,号漪园、澹园)《玉堂丛语》记载:陈音(字师召,号愧斋)先生性格宽厚坦荡,在翰林院任职时,夫人曾经试探他。正值宾客到来,陈先生呼唤上茶,夫人回答说还没有煮,先生就说也罢。又呼唤要干茶,夫人回答说未买,先生就说也罢。客人为之捧腹大笑,当时人称他为陈也罢。
明代沈周(字启南,号石田)《客坐新闻》记载:吴地的高僧大机的居处,有古屋三四间,非常洁净,不能吐唾沫。他擅长烹茶,有清澈甘洌的古井供其使用。宾客到来,就端出一瓯供奉品饮,令人荡涤肠胃,感觉清爽。我父亲与他交往很久,也嗜好饮茶,每次入城,必定到他的居处品饮。
沈周《书茶别论后》写道:自古名山胜地,都留着等待流放贬官的人,而茶叶,则是专门供奉高人隐士的,所以说造物的神仙都是有其深意的。周庆叔编撰《茶别论》,以流传天下,我料想看重金钱的富贵人家是没有此种清福了,也恐怕那些只图贪多畅快,不知品味的俗人,未必能够领略此中真味。而周庆叔隐居长兴,所到之处携带茶具,邀请我到素瓯黄叶之间,共相欣赏。遗憾的是陆羽(字鸿渐)、蔡襄(字君谟)无法见到庆叔,不禁为之倾茶三叹。
明代冯梦祯《快雪堂漫录》记载:李攀龙(字于麟,号沧溟,山东历城人)到我们浙江担任按察副使,徐中行(字子与)以最上品的茶赠给他。等到徐中行与他在昭庆寺见面时问及,却已经赏给皂隶吏役了。大概是因为茶从外表看叶大梗多,李攀龙是北方士人,得不到重视也就自然了。记录于此,聊发一笑。
明末闵元衡《玉壶冰》中说:良宵闲坐,点着篝火烹煮茶叶,这时万籁俱寂,远处稀疏的钟声不时传来,当此情景,对着简编读书而不知疲倦,彻夜不用睡觉,这也是一种快乐啊!
清代劳大舆《瓯江逸志》记载:永嘉(今浙江温州)每年进贡茶芽十斤,乐清进贡茶芽五斤,瑞安、平阳每年进贡茶芽也是一样。
雁荡山的五珍是:龙湫茶、观音竹、金星草、山乐官(一种鸟)、香鱼。这里说的龙湫茶就是明茶,紫色而芳香,叫做玄茶,其味道都与天池茶相似而略显淡薄。
明代王世懋(字敬美,太仓人)《二酉委谭》记载:我生性耐不住冠带整齐,尤其是在盛夏酷暑的时候,江西天气热得早,而今年更甚。春三月十七日,在滕王阁请客饮酒,太阳出来如火一样,大汗流至脚跟,头上涔涔的汗水让人几乎不知所措。归来后非常烦闷,妻子为我烧水沐浴,于是就披发裸身前去。当时西山云雾新茶刚到,张右伯正好寄赠给我,茶色鲜白,有豆子香味,差不多可以与虎丘茶相媲美。我沐浴出来,凌露坐在明月之下,急忙让侍从汲取新水烹茶品尝。感觉清凉的气息沁人心脾,两腋习习风生。于是感念此种况味,都不是官场宦海所能体味得到的。蔡琳泉先生年老而更加嗜好饮茶,比我更甚。只是当时已经就寝,无法邀请他相对品饮。清晨起来再次煮水烹茶,但是已经风味不同了。追忆夜间品饮的风味,修书一通赠给先生。
明代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记载:王,昌邑(今属山东)人。明太祖洪武初年,担任宁波知府。有下属来谒见奏事,就烹茶以待。当得知下属在为客人居间说情,王大呼撤去,下属深感惭愧而退。王也因此被称为“撤茶太守”。
《临安志》记载:栖霞洞内有水洞,深不可测,其中的水极为甘甜清洌,魏公曾经烹此水点茶。
明代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馀》记载:杭州早年有酒馆而没有茶坊,但是富贵之家举行宴会,依然有专供茶事的人,称为茶博士。
《潘子真诗话》记载:叶涛所作的诗非常不工整,却喜欢吟咏。他曾经作有一首《试茶》诗,其中有“碾成天上龙兼风,煮出人间蟹与虾”的句子。有好事的人嘲笑他说:“这不是试茶,这是碾玉的匠人在吃南方的食品呢!”明代董其昌《容台集》记载:蔡襄(谥忠惠)进贡小龙团茶,以至于被苏轼(谥文忠)所讥讽,认为他与钱惟演(字希圣,谥思)进贡姚黄花(即牡丹名品姚黄)一样,失去了士人的气节。但是宋朝时君臣之间的关系,情意和合,还可以从此窥见一斑。况且蔡襄也并没有因为贡茶而求得恩宠,只是点缀太平世界的一段清心雅事罢了。苏轼曾经书写欧阳修的滁州二记(《醉翁亭记》《丰乐亭记》),知道他不愿意书写《茶录》,我就以苏轼的笔法书写《茶录》,为蔡襄先生忏悔。否则的话,苏轼的蛰龙诗句(指苏轼《咏桧》诗中有“根到九曲无曲处,世间惟有蛰龙知”,因此下狱),几乎濒临汤火(指苏轼下狱后所做《绝命诗》“梦绕云山心似鹿,魂飞汤火命如鸠”),又有什么罪过呢?大凡持论,不能太远离人情物理才可以。
金陵(今江苏南京)春卿署(指南京礼部)中,不时有以松萝茶相赠的,都香味平常罢了。致仕归来居于山馆,反而得以品尝到茶中极品,经询问才知道是闵汶水所收藏的珍品。闵汶水家居金陵,与我不远,作为隐逸之士就像海上之鸥飞舞而不下来,因为知道物以稀为贵,很少与富贵之人交游。从前陆羽以为精于茶事,为贵人所侮辱,愤而写下《毁茶论》,至于像闵汶水,我知道他终究也不会作此毁茶之论的。
明代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记载:摄山(即南京紫金山)栖霞寺有一处茶坪,茶叶生长在荆棘林莽中,不曾经过人工修剪种植。唐代陆羽曾经来此入山采摘,皇甫冉则写有《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》赠给他。
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》记载:泰山不出产茶叶,山中的人们采摘青桐芽烹饮,称为女儿茶。又有松苔,也被当做茶叶饮用,非常富有奇韵。
明代钟惺(字伯敬,号退谷,竟陵人)《钟伯敬集》中有《茶讯》诗写道:“犹得年年一度行,嗣音幸借采茶名。”钟惺与徐波(字元叹)交情深厚,从吴中到楚地相距数千里,二人以买茶为名,一年通一次音讯,于是成为佳话,叫做茶讯。
我曾经见过钱谦益的《茶供说》中写道:娄江逸人朱汝圭精于茶事,将因为饮茶而归隐,想请我给他写一篇文章,并表示愿意每年采摘诸山的青芽,为我作供。我观察佛坛中所设置的供品,取白色的牛奶、砂糖、纯蜜之类;西方的沙门、婆罗门,则用葡萄、甘蔗作为供品,还不曾有过以茶为供品的。
陆羽,是生长于佛寺的佛家弟子,诗僧皎然(姓谢名昼,居抒山妙喜寺),是杼山的禅师,而陆羽的《茶经》,皎然的《茶歌》,也都没有说道以茶供佛。西土以贯花燃香供佛,而不以茶供,这也是供奉之典制的缺失。朱汝圭精心置办茶事,金芽素瓷,清净供佛,来生必然受到好报,往生香国,以各种奇妙的香料供佛,难道只是像丹丘羽人那样饮茶,而生羽翼罢了呢?我不敢作为朱汝圭的茶供对象,只请以茶来供佛。后世精于茶道的人,以采茶供佛作为佛事活动,那么也是从我感念朱汝圭开始的。于是就写下这篇《茶供说》赠给他。
释普济《五灯会元》记载:摩突罗国有一片林木青翠枝叶茂盛的地方,叫做优留茶。
有僧人问吉州如宝禅师说:“如何是和尚家风?”禅师回答说:“饭后三碗茶。”僧人又问大道谷泉禅师说:“不知道宾客到来如何款待?”禅师回答说:“云门胡饼赵州茶。”清代张英等《渊鉴类函》记载:唐代诗人郑愚《茶诗》写道:“嫩芽香且灵,吾谓草中英。夜臼和烟捣,寒炉对雪烹。”于是就称茶为草中英。
素馨花叫做裨茗,陈献章(字公甫,号石斋,新会白沙人,世称陈白沙)《素馨记》认为这种花能够稍微有助于茶罢了。也叫做那悉茗花。
清代张玉书等《佩文韵府》记载:元好问诗注中说:“唐朝人以茶作为小女孩的美称。”《黔南行记》记载:陆羽《茶经》记载黄牛峡(今湖北宜昌西)的茶叶可以品饮,于是命船夫前去寻求。有一位老妇人卖新茶一笼,与草叶没有差别,只是山中没有好事者罢了。
起初我在峡州(今湖北宜昌),向士大夫打听黄陵茶,都说粗涩不可以品饮。又试问小吏,说是只有僧人所采制的茶叶味道好。命人寻求,获得十饼,价格很平常。于是携带茶饼到黄牛峡,把风炉放在林荫之下,亲自煎水候汤,依法烹试。以茶祭奠过黄牛神之后,再来品啜。元明尧夫说:其香味不减江南茶。由此可知夷陵的士大夫不免以貌取之了。
南宋周必大《九华山录》记载:到化城寺,拜谒金地藏塔,僧人祖瑛献上当地土产的茶叶,味道可以与北苑贡茶媲美。
明代冯时可《茶录》记载:松江府(今上海)余山也出产茶叶,与苏州天池茶没有差异,只是采摘制造不如天池。近年有僧人到来,以虎丘茶的制法采制,香味与松萝茶略等。老和尚急忙把他驱逐出去,说:“不要让此山陷入红尘之中、火坑之内。”清代冒襄(字辟疆,号巢民)《界茶汇钞》记载:回忆四十七年前,有一个姓柯的吴地人,对阳羡的茶山非常熟悉,每年桐花初发的时候,为我进入山,用箬叶茶笼带来十多种茶叶。其中最为精致的茶叶,不超过一斤或者数两罢了。味道精到,香气馥郁,兼具芝兰金石之性。十五年如一日,坚持不懈。后来董小宛从苏州与我结合,茶必须苏州半塘顾先生负责制作,黄熟香则必须金平叔负责制作,茶香双妙,更加精微异常。但是顾、金两家所供应的茶和香,每年一定要先供奉钱谦益(号牧斋,居常熟虞山)夫人柳如是、我们同郡的陇西旧姬以及我和夫人董小宛,而后才供应其他人。
金沙于象明带来茶,品质绝妙。金沙于氏精于鉴赏,驰名江南,而山的棋盘顶,其地久归于家,每年于象明的父母必定亲自采摘制造。今年夏天,他带来庙后、棋盘顶、涨沙、本山等品种,各有等次,但都是道地的茶,极真极妙,乃二十年来所没有过的。另外他还辨别水品,把握火候,亲手洗茶,烹点细致洁净,从而使得茶的色香性情,根据文人的奇异嗜好,一一淋漓而出。正如丹丘羽人所谓饮茶能生羽翼者,真是老年的一种称心乐事啊!
苏州七十四岁的老人朱汝圭带着茶叶来拜访。他的茶和于象明的差不多,只是多了花香一种。朱汝圭从小嗜好饮茶,就像是世人所谓的胎里素,十四岁进入山,到如今已经过一百二十番春夏,始终不渝,超过了食色的本性,唯好饮茶。有子孙是著名的生员,到老也不接受他们的赡养,因为他们不嗜好饮茶,不像爷爷。每次壮胆入山,与老虎猛兽周旋,然后背着茶笼来到茶肆,以茶香啸傲同道。每天从早到晚洗茶涤器,品啜无休,指爪齿颊留有余香,言语激扬,文字赞颂,滔滔不绝,总有喜神妙气与茶相辅相成,益智养心,这是一种奇异的癖好。
清代吴震方《岭南杂记》记载:潮州灯节,把漂亮的儿童装扮成采茶女,每队十二人或者八人,手提花篮,分部前进并歌唱,俯仰进退,抑扬顿挫,非常妖艳。另外以稍微年长者二人作为队长,高举彩灯,灯上点缀着扶桑、茉莉等花。采茶女的进退行止,都要视队长而定。他们到各个衙门或者富贵人家进行演唱,人家则赏赐银钱、酒食、茶果。从正月十三日晚起,到十八日晚结束。我记录其词曲数首,颇有《前溪》、《子夜》的遗风。
明代郎瑛《七修类稿》(一作周亮工《闽小记》,是)记载:徽州歙县人闵汶水,居住在金陵桃叶渡上。我曾经去他家品茶,见其煎水候火,都亲自操作,用小酒杯请客人品啜,很专业的烹饮情态,正如德山和尚宣鉴担青龙钞,自矜清高罢了,不足为奇。秣陵(今江苏南京)的好事者,曾经讥讽福建无茶,说闽客(福建的客人)得到闵茶(闵汶水的茶)都制成罗囊盛起来,佩戴在身上代替檀香。其实福建人并不重视闵汶水。福建的客人游历南京的,宋彀(字比玉,号荔枝仙)、洪仲章等人,都是依附吴人强作解事,贬低家鸡,而以野鹜为贵,受到讥讽也是应该的。南京三山街的薛老,也是秦淮河上的闵汶水。薛老曾经说过闵汶水假借其他的调味品制作出兰香茶,终究使得茶的真味丧失净尽。如果闵汶水在世,听到此话也应当感到羞愧。薛老曾经居住在,亲自修剪茶树,焙制茶叶,想要凌驾于闵汶水之上。我认为茶叶很难以香味闻名,何况以兰花香来确定茶香的品位,乃是咫尺之见,所以我认为薛老的观点为好。
延邵(今属福建)人称呼制茶的人叫做碧竖,南唐攻灭富沙王王延政后,碧竖都成了绿林好汉。
蔡襄(谥忠惠)《茶录》石刻镶嵌在瓯宁(今福建建瓯)县城学校的墙壁间。我在五年前曾经拓了多张寄赠给知己,如今已经漫漶不如以前了。
福建所产的酒各郡都一样,所产的茶也是如此。今年我得茶很多,学习苏轼义酒的故事,全部合而为一,但是合不合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两样。
清代李仙根(字南津,号子静)《安南杂记》记载:交趾称呼其富贵之人为翁茶。所谓翁茶,就是大官的意思。
清代陈鉴《虎丘茶经补注》记载:徐有贞(字元玉,号天全老人)从金齿(今云南保山)贬谪之地回来,每年的春末夏初,就到虎丘开设茶社。
罗光玺作《虎丘茶记》,嘲讽山僧有替身茶。
吴宽(字原博,号匏庵)与沈周(号石田)一起游历虎丘,亲自采茶煎水对饮,自己说有茶癖。
清代王士祯《渔洋诗话》记载:林确斋,其名佚,江西人。居住在冠石,率领子孙种茶,亲自拿着农具,挑着担子,夜间则诵读《毛诗》、《离骚》。经过冠石的人们,都能看到三四个少年,头上裹着一幅布,赤着脚,挥锄耕耘,一边歌声琅然,有金石之韵,无不私下感叹,以为这是古代图画中的人物。
清代尤侗《尤西堂集》中有《戏册茶为不夜侯制》。
清代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记载:上巳后三天,新茶从马上运来,新茶到来之日宫中的价格是五十两银子,宫外则达二三十两。不过一两天,就跌到二三两了。见《北京岁华记》。
朱彝尊《曝书亭集》记载:无锡惠山寺听松庵高僧性海,自制竹火炉,中书舍人王绂过访,见而爱之,为他画山水横幅,并且题诗纪念。年久竹炉损坏,侍郎盛冰壑根据旧炉更新其制,流传到京师,各位公卿大臣多有诗词吟咏。典籍顾贞观(字华封,号梁汾)仿照其旧制制成竹炉,等来到京师,侍卫纳兰性德(字容若,又作成容若、楞伽山人)以旧图赠给他。丙寅的秋天,顾贞观带着竹炉及图卷过访余海波寺寓,正好姜宸英(字西溟,号湛园)、周(字青士,号谷)、孙恺似三个人也到了。打坐青藤之下,烧炉烹试武夷茶,共同联句成四十韵,书写于册页之上,用来给那些好事的博雅君子欣赏。
清代蔡方炳《增订广舆记》记载:湖广长沙府攸县,古迹有茶王城,也就是汉代的茶陵城。
清代葛万里《清异录》记载:倪瓒(字元镇)饮茶要加进果子,叫做清泉白石。如果不是佳客不予招待。一次,有客人请见,命进献此茶,客人口渴,两口喝完,倪瓒心中非常后悔,就收起茶盏入内。
黄周星(字九烟,号而庵)梦读《采茶赋》,只记得其中的一句,叫做“施凌云以翠步”。
葛万里《别号录》记载:宋代曾几,字吉甫,别号茶山。明代许应元,字子春,别号茶山。
《随见录》记载:武夷山五曲朱文公书院内,有一棵茶树,茶叶有臭虫气,等到经过焙制,出来时比其他树上的茶叶更香,名叫臭叶香茶。另外还有老树多棵,据说是朱熹亲手种植,名叫宋树。
明代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》记载:立夏之日,家家户户都烹试新茶,配合各种精细水果,馈送亲戚和邻居,叫做七家茶。
宋代杭州南屏山净慈寺和尚谦师精干茶事,自己说得心应手,不是言语传达和学习能达到的。
刘士亨有《谢上人惠桂花茶》诗写道:“金粟金芽出焙篝,鹤边小试兔丝瓯。叶含雷信三春雨,花带天香八月秋。味美绝胜阳羡种,神清如在广寒游。玉川句好无才续,我欲逃禅问赵州。”明末清初李世熊《寒支集》记载:新城的山中有一种奇异的鸟,其叫声如同吹萧,于是这座山就叫做萧曲山。山中也出产好茶,也叫做萧曲茶。因此作歌记录此事。
《禅玄显教编》记载:徐道人居住在庐山天池寺,不吃饭食已经有九年了。养了一只墨羽鹤,曾经采摘山中的新茶,让鹤衔着松枝烹茶。遇到道友,就一起饮上几碗。
清代张鹏《抑斋集》中有《御赐郑宅茶赋》写道:“青云幸接于后尘,白日捧归乎深殿。从容步缓,膏芬齐出螭头;肃穆神凝,乳滴将开蜡面。用以濡毫,可媲文章之草;将之比德,勉为精白之臣。”
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