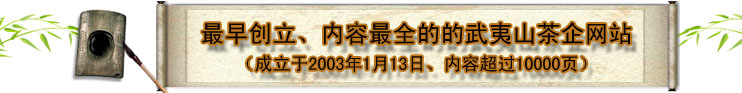|
闻龙《茶笺》:东坡云:“蔡君谟嗜茶,老病不能饮,日烹而玩之,可发来者之一笑也。”孰知千载之下有同病焉。余尝有诗云:“年老耽弥甚,脾寒量不胜。”去烹而玩之者几希矣。因忆老友周文甫,自少至老,茗碗薰炉,无时暂废。饮茶日有定期:旦明、晏食、禺中、晡时、下舂、黄昏,凡六举,而客至烹点不与焉。寿八十五,无疾而卒,非宿植清福,乌能毕世安享?视好而不能饮者,所得不既多乎!尝蓄一龚春壶,摩挲宝爱,不啻掌珠。用之既久,外类紫玉,内如碧云,真奇物也,后以殉葬。
《快雪堂漫录》:昨同徐茂吴至老龙井买茶,山民十数家,各出茶。茂吴以次点试,皆以为赝,曰:真者甘香而不冽,稍冽便为诸山赝品。得一二两以为真物,试之,果甘香若兰。而山民及寺僧反以茂吴为非,吾亦不能置辨。伪物乱真如此。茂吴品茶,以虎丘为第一,常用银一两馀购其斤许。寺僧以茂吴精鉴,不敢相欺。他人所得虽厚价,亦赝物也。子晋云:本山茶叶微带黑,不甚青翠。点之色白如玉,而作寒豆香,宋人呼为白云茶。稍绿便为天池物。天池茶中杂数茎虎丘,则香味迥别。虎丘,其茶中王种耶!茶精者,庶几妃后;天池、龙井,便为臣种,其馀则民种矣。
熊明遇《山茶记》:茶之色重、味重、香重者,俱非上品。松萝香重;六安味苦,而香与松萝同;天池亦有草莱气,龙井如之。至云雾则色重而味浓矣。尝啜虎丘茶,色白而香似婴儿肉,真称精绝。
邢士襄《茶说》:夫茶中着料,碗中着果,譬如玉貌加脂,娥眉染黛,翻累本色矣。
冯可宾《茶笺》:茶宜无事、佳客、幽坐、吟咏、挥翰、徜徉、睡起、宿酲、清供、精舍、会心、赏鉴、文僮。茶忌不如法、恶具、主客不韵、冠裳苛礼、荤肴杂陈、忙冗、壁间案头多恶趣。
谢在杭《五杂俎》:昔人谓:扬子江心水,蒙山顶上茶。蒙山在蜀雅州,其中峰顶尤极险秽,虎狼蛇虺所居,采得其茶,可蠲百病。今山东人以蒙阴山下石衣为茶当之,非矣。然蒙阴茶性亦冷,可治胃热之病。
凡花之奇香者,皆可点汤。《遵生八笺》云:“芙蓉可为汤。”然今牡丹、蔷薇、玫瑰、桂、菊之属,采以为汤,亦觉清远不俗,但不若茗之易致耳。
北方柳芽初茁者,采之入汤,云其昧胜茶。曲阜孔林楷木,其芽可以烹饮。闽中佛手柑、橄榄为汤,饮之清香,色味亦旗枪之亚也。又或以豆微炒,投沸汤中,倾之,其色正绿香味亦不减新茗。偶宿荒村中觅茗不得者,可以此代也。
《谷山笔麈》:六朝时,北人犹不饮茶,至以酪与之较,惟江南人食之甘。至唐始兴茶税。宋元以来,茶目遂多,然皆蒸干为末,如今香饼之制,乃以入贡,非如今之食茶,止采而烹之也。西北饮茶,不知起于何时。本朝以茶易马,西北以茶为药,疗百病皆瘥,此亦前代所未有也。
《金陵琐事》:思屯,乾道人,见万手软膝酸,云:“系五藏皆火,不必服药,惟武夷茶能解之。”茶以东南枝者佳,采得烹以涧泉,则茶竖立,若以井水即横。
《六研斋笔记》:茶以芳冽洗神,非读书谈道,不宜亵用。然非真正契道之士,茶之韵味,亦未易评量。尝笑时流持论,贵嘶声之曲,无色之茶。嘶近于哑,古之绕梁遏云,竟成钝置。茶若无色,芳冽必减,且芳与鼻触,冽以舌受,色之有无,目之所审。根境不相摄,而取衷于彼,何其悖也!何其谬耶!
虎丘以有芳无色,擅茗事之品。顾其馥郁不胜兰芷,与新剥豆花 同调,鼻之消受,亦无几何。至于人口,淡于勺水,清冷之渊,何地不有,乃烦有司章程,作僧流捶楚哉?
《紫桃轩杂缀》:天目清而不,苦而不螫,正堪与淄流漱涤。笋蕨、石濑则太寒俭,野人之饮耳。松萝极精者方堪入供,亦浓辣有馀,甘芳不足,恰如多财贾人,纵复蕴藉,不免作蒜酪气。分水贡芽,出本不多。大叶老根,泼之不动,人水煎成,番有奇味。荐此茗时,如得千年松柏根作石鼎熏燎,乃足称其老气。
“鸡苏佛”、“橄榄仙”,宋人咏茶语也。鸡苏即薄荷,上口芳辣。橄榄久咀回甘。合此二者,庶得茶蕴,曰仙,曰佛,当于空玄虚寂中,嘿嘿证人。不具是舌根者,终难与说也。
赏名花不宜更度曲,烹精茗不必更焚香,恐耳目口鼻互牵,不得全领其妙也。
精茶不宜泼饭,更不宜沃醉。以醉则燥渴,将灭裂吾上味耳。精茶岂止当为俗客吝?倘是日汨汨尘务,无好意绪,即烹就,宁俟冷而灌兰,断不令俗肠污吾茗君也。
罗山庙后精者,亦芬芳回甘。但嫌稍浓,乏云露清空之韵。以兄虎丘则有馀,以父龙井则不足。
天池通俗之才,无远韵,亦不致呕哕寒月。诸茶晦黯无色,而彼独翠绿媚人,可念也。
屠赤水云:茶于谷雨候晴明日采制者,能治痰嗽、疗百疾。
《类林新咏》:顾彦先曰:“有味如,饮而不醉;无味如茶,饮而酲焉。”醉人何用也。
《徐文长秘集·致品》:茶宜精舍,宜云林,宜磁瓶,宜竹灶,宜幽人雅士,宜衲子仙朋,宜永昼清谈,宜寒宵兀坐,宜松月下,宜花鸟间,宜清流白石,宜绿藓苍苔,宜素手汲泉,宜红妆扫雪,宜船头吹火,宜竹里飘烟。
《芸窗清玩》:茅一相云:余性不能饮酒,而独耽味于茗。清泉白石可以濯五脏之污,可以澄心气之哲。服之不已,觉两腋习习,清风自生。吾读《醉乡记》,未尝不神游焉。而间与陆鸿渐、蔡君漠上下其议,则又爽然自释矣。
《三才藻异》:雷鸣茶产蒙山顶,雷发收之,服三两换骨,四两为地仙。
《闻雁斋笔谈》:赵长白自言:“吾生平无他幸,但不曾饮井水耳。”此老于茶,可谓能尽其性者。今亦老矣,甚穷,大都不能如曩时,犹摩挲万卷中,作《茶史》,故是天壤间多情人也。
袁宏道《瓶花史》:赏花,茗赏者上也,谭赏者次也,酒赏者下也。
《茶谱》:《博物志》云:“饮真茶,令人少眠。”此是实事,但茶佳乃效,且须末茶饮之。如叶煮者,不效也。
《太平清话》:琉球国亦晓烹茶。设古鼎于几上,水将沸时投茶末一匙,以汤沃之。少顷奉饮,味清香。
《藜床渖馀》:长安妇女有好事者,曾侯家睹彩笺曰:一轮初满,万户皆清。若乃狎处衾帷,不惟辜负蟾光,窃恐嫦娥生妒。涓于十五、十六二宵,联女伴同志者,一茗一炉,相从卜夜,名曰伴嫦娥。凡有冰心,仁垂玉允。朱门龙氏拜启。[原注:陆浚原。]沈周《跋茶录》:樵海先生,真隐君子也。平日不知朱门为何物,日偃仰于青山白云堆中,以一瓢消磨半生。盖实得品茶三昧,可以羽翼桑苎翁之所不及,即谓先生为茶中董狐可也。
王《快说续记》:春日看花,郊行一二里许,足力小疲,口亦少渴。忽逢解事僧邀至精舍,未通姓名,便进佳茗,踞竹床连啜数瓯,然后言别,不亦快哉!
卫泳《枕中秘》:读罢饮馀,竹外茶烟轻扬;花深酒后,铛中声响初浮。个中风味谁知,卢居士可与言者;心下快活自省,黄宜州岂欺我哉?
江之兰《文房约》:诗书涵圣脉,草木栖神明。一草一木,当其含香吐艳,倚槛临窗,真足赏心悦目,助我幽思。亟宜烹蒙顶石花,悠然啜饮。
扶舆沆瀣,往来于奇峰怪石间,结成佳茗。故幽人逸士,纱帽笼头,自煎自吃。车声羊肠,无非火候,苟饮不尽且漱弃之,是又呼陆羽为茶博士之流也。
高士奇《天禄识馀》:饮茶或云始于梁天监中,见《洛阳伽蓝记》,非也。按《吴志·韦曜传》:“孙皓每宴飨,无不竟日,曜不能饮,密赐茶以当酒。”如此言,则三国时已知饮茶矣。逮唐中世,榷茶遂与煮海相抗,迄今国计赖之。
《中山传信录》:琉球茶瓯颇大,斟茶止二三分,用果一小块贮匙内。此学中国献茶法也。
王复礼《茶说》:花晨月夕,贤主嘉宾,纵谈古今,品茶次第,天壤间更有何乐?奚俟脍鲤羔,金玉液,痛饮狂呼,始为得意也?范文正公云:“露芽错落一番荣,缀玉含珠散嘉树。斗茶味兮轻醍醐,斗茶香兮薄兰芷。”沈心斋云:“香含玉女峰头露,润带珠帘洞口云。”可称岩茗知己。
陈鉴《虎丘茶经注补》:鉴亲采数嫩叶,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,真作豆花香。昔之鬻虎丘茶者,尽天池也。
陈鼎《滇黔纪游》:贵州罗汉洞,深十馀里,中有泉一泓,其色如黝。甘香清冽。煮茗则色如渥丹,饮之唇齿皆赤,七日乃复。
《瑞草论》云:茶之为用,味寒。若热渴、凝闷胸、目涩、四肢烦、百节不舒,聊四五暖,与醍醐甘露抗衡也。
《本草拾遗》:茗味苦,微寒,无毒,治五脏邪气,益意思,令人少卧,能轻身、明目、去痰、消渴、利水道。
蜀雅州名山茶有露芽、芽,皆云火之前者,言采造于禁火之前也。火后者次之。又有枳壳芽、枸杞芽、批把芽,皆治风疾。又有皂荚芽、槐芽、柳芽,乃上春摘其芽,和茶作之。故今南人输官茶,往往杂以众叶,惟茅芦、竹箬之类,不可以入茶。自馀山中草木、芽叶,皆可和合,而椿、柿叶尤奇。真茶性极冷,惟雅州蒙顶出者,温而主疗疾。
李时珍《本草》:服葳灵仙、土获苓者,忌饮茶。
《群芳谱》:疗治方:气虚、头痛,用上春茶末,调成膏,置瓦盏内覆转,以巴豆四十粒,作一次烧,烟熏之,晒干乳细,每服一匙。别入好茶末,食后煎服,立效。又赤白痢下,以好茶一斤,炙捣为末,浓煎一二盏服,久痢亦宜。又二便不通,好茶、生芝麻各一撮,细嚼,滚水冲下,即通。屡试立效。如嚼不及,擂烂,滚水送下。
《随见录》:《苏文忠集》载,宪宗赐马总治泄痢腹痛方: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,用一大钱并草茶相等煎服。元二年,文潞公得此疾,百药不效,服此方而愈。

|